

2022年,于我来说是特别的一年。这一年,我经历了本科毕业到研究生开学,从本科生到研究生身份的转折;这一年,我经历了从讲台下听讲到走上讲台做校园阅读分享发言,老师给予的诸种鼓励……这一年,我好像刚刚捋清楚自己本科四年是如何度过的,虽然那四年间的很多片段也只剩浮光掠影。如今,作为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如何进行我这已经开启的三年时光是我面临的问题,未来,总是充满未知与抉择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身份转换中,我以远程线上的方式旁听了一场关于校园生活的讲座: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主办,南山书屋·象山之家阅读空间、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会、艺术与管理教育学院研究生会承办,于2022年12月1日在南山书屋·象山之家阅读空间举行的“校园生活中的学与问“对谈活动,主持人是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王犁,对谈人有浙江文学院院长程士庆、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管怀宾和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封治国。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因为兴趣而选择自己所学习的专业,但就像程士庆所说:“我的女儿是学美术的,以我作为父亲的感受,大家考到中国美院,至少是历经千辛万苦。大家走入美院,美术方面肯定是你们从小的兴趣,坚持到现在,在座的各位是幸福的,学习能够跟自己的兴趣结合起来是最幸福的事情。”
我们为何选择这个专业?或许是因为未来人们所说的“好就业”,但倘若凭借着兴趣,未来又在何方?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封治国觉得在美院的“学”和“问”,不是见到老师一定要提问题,而是一种疑问和反叛。王犁则认为对于专业的野心是需要在本科阶段就开始铺垫的,“未来在我所从事的领域里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需要思考的,而现在很多同学在等着期末考试,这其实是一个问题。我经常跟我们学院的本科生说,千万不要把本科读成中学,本科是为未来做铺垫,不要把精力放在考试上,你未来要在这个学科扮演什么角色,这是需要野心的。”

关于“野心”,封治国举了邱振中的例子:当年浙江美院恢复高考,邱振中作为浙江美院第一年招收的书法研究生,他当时想他们这帮人能够为中国书法史做什么。那个年代,邱振中的那一批同学、那一批研究生都有这个想法。那时候上大学也好、读研究生也好,首先都给自己设计了很明确的要求。但是现在很多学生都太乖了,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应该“野”一些。封治国以中国美院为例,他说:“我们很多著名的老师和艺术家都在他们学生时期是叛逆的,是我们很多人眼中的‘问题学生’。”封治国还提到油画家崔小冬和常青在学生时期的故事。“为什么八五新潮能在中国美院激起浪花?因为这帮人虽然‘野’,但是他们心性高、眼光准。”
环境与兴趣似乎总是这样相辅相成。王犁在对谈开始时提到他最近看到一个家长微信朋友圈:觉得中国美院有担当,疫情三年自己的女儿来一直是线下教学,而我们的毕业展也一直是线下的展览。封治国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面有我们学院的担当,因为我们中国美院坚持自己的判断、坚持自己的做法。我们在各地线上云集的情况下还举办线下毕业展览,这是美院的品格,我们在美院学习需要保持这种独立的品格。”
无论是大学生活还是研究生生活,都是校园生活的一种。但是这种校园生活又与我们中小学时期的校园生活不同,如何度过、如何面对,是很多人不曾想或想不出答案的问题。程士庆认为我们现在的大学是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是双重的研究,需要提出问题、再解决问题。因此“鱼与渔”是他在对谈之初就抛出的两个观点。第一个“鱼”他认为相当于今天对谈主题中的“学”,而第二个“渔”,是“问”,学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于能力的问题。关于能否在学习过程中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程士庆说:“我读书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末,文学的效应还在,我那时在校园里到处联谊,作为文学青年办文学报刊等等。所以我待在南京大学的时间并不多,每次临近考试我就借同学的笔记,为考试作准备。基本上到大学以后时间很多是自己可以安排的,这时候我们自身的能力就很重要了,我是学中文的,办报刊、搞创作,学以致用,后来也很巧,我当时投稿给广州的《随笔》杂志,也是机缘,被发表在封面推荐的文章里。结果我毕业后去了那里工作,这个杂志就是花城出版社办的。这是一种机缘促使的偶然,王犁将其解释为,“偶然性会在每一个人身上发生,但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你有没有给你的偶然性埋下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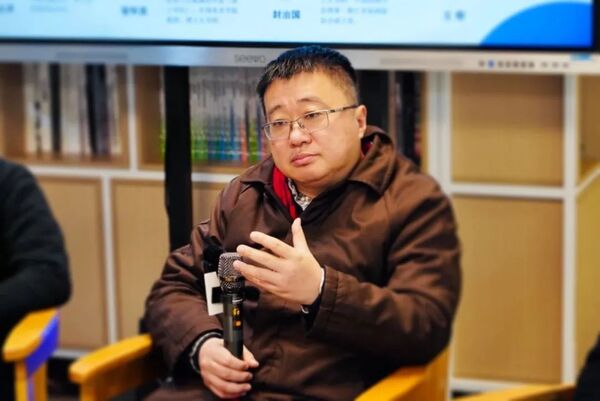
虽然管怀宾考上美院时已经24岁了,读研究生时三十多岁、读博士四十多岁,但对于他来说:“我从中国美院毕业后到了今天的江南大学当老师,后来因为偶然的机遇去了日本,待了近十年,我从语言学开始,然后在那里读硕士,后来又读博士。我当时就是想走出我的世界,去跟更优秀的环境和更优秀的人去接触。我常常跟我的研究生交流,很多时候需要把一些东西激发出来,你跟人和社会的接触实际上就是在找这个东西。所以我说,我比较幸运,我小时候的爱好成为伴随我一生的东西。”
管怀宾、封治国和王犁都是从县城起步,经历千辛才进入中国美院学习,后来又因为“偶然”在此任教至今。封治国回忆自己的学画经历,他说:“我们县城里面小人书的书摊是我文学启蒙和绘画启蒙生发地。电影院我最为热爱的部分就是看到门口海报的更换,因为海报是画的。我通过小人书和电影院的海报很自然的对绘画产生了兴趣。小时候还喜欢看点书,我高中有段时间喜欢新诗,那时候还给《星星》诗刊投过稿,很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生活有“偶然”,但没有“意外”。我们所经历的、所正在从事的,所谓的梦想与追梦,都在为我们的未来埋下一个偶然的种子。程士庆说,对于美术类学生来讲,本科和研究生经历,除了学习美术专业技巧外,应该走向社会,在社会中增加自己的经历,让梦想落地。
阅读是作为学生来说无法绕开的话题,读什么、怎么读?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都为时不晚。封治国认为,我们每个人从哪里开始,没有标准答案,阅读从哪里开始,更没有标准答案。艺术反应的不是生活,恰恰是观察者自身。只要有毅力,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
管怀宾说,虽然他会给他的学生开书单,但是再完美的书单、再完美的课程都无法让人成为当代的艺术家、优秀的设计师。“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当它成为知识、当知识开始传播,就已经成为过去式。如何在过去当中找到创造的可能性,这是学生与老师需要碰撞的。我们是视觉艺术,我们的学问不仅仅是在谈论当中。我经常让研究生做研究计划,有人会说一年级读书、二年级创作,完全根据学校步骤的。高考是验证你前面十几年的学习,但本科和研究生是没有这个验证的,这个验证是在未来的几十年去验证的。”
阅读如此,那么研究生期间,我们该如何度过?什么事情是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比较重要的?我想,虽然未来总是迷茫的,但倘若真有个切实答案,探索生活的乐趣或许也会变得有些乏味。

封治国博士念的是美术史专业,在那个阶段,他想短暂离开绘画,从另一个角度,做其他事情。封治国说,“我在美术史论系读博士是有一个野心的,我不希望在我答辩的时候,我的老师出来帮我打圆场,说他是画油画的,这是我的最低要求。如果是那样,我都能想到我会面对的质疑——那他回去画油画就好了。”

很多人看到封治国只用了三年就按期毕业,但用封治国自己的话来讲:“博士我读了三年,但是在我博士之前我做了六七年的准备。”对于封治国的博士论文,他给自己设定了三个目标:第一,每个人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是要有定位的,我当时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会思考潜在的读者,我希望这个领域内第一流的专家看到我的论文,甚至这个第一流未必是你自己的导师。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中是要有所不同的,我希望得到他们充分的肯定。人家谈过的东西我一定是概括去写,如果一定要做以前的史料,那么我能否能使它产生新的意义。第二,一定要有所发现,在历史学领域里面,无论你有多么天才的想法也一定是依托自己的实践学习,如果能发现文献群中不一样的意义,那么就会变得有点意思。第三,我要经得起第一流学者的拷问。在西方博士论文答辩中有一个指标ambition,雄心和野心是一个东西。好的博士论文中就有这个野心。
对于硕士论文,管怀宾说在论文开题之前是需要有大量实践积累的,这样才会使你的论文有内容,不然理论知识的系统和我们的技能就会产生分离。研究生的论文是需要有思想的。王犁说,你的导师给你的要求可能是一般的要求或优秀的要求,但你自己的要求是什么?你有没有为你的未来做要求。就像当你完成专业阅读之后,需要有文学爱好,要去看诗歌,要去看小说,特别是在中国的环境中,小说能让你更加了解社会,还要读历史,不要一个学科就把自己框住了。

对于日常习作和毕业创作,封治国认为日常学习是一个积累,但创作是一个角度。在美院的系统中,每一个学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在完成日常的系统之外,我们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点,作为你的命题、作为将来毕业展陈的内容。这不是跟课程作业那样范范地去呈现,而是深究的内容,所有的课题和知识都需要我们自己的消化系统过后吐纳。为什么现在一些学生的文章看着像八股文?因为阅读太少。封治国说陈丹青的硕士毕业的创作谈和崔小冬的硕士论文给了他深刻印象:“读完你会发现文章里面是有问题意识的,是活生生的人写的东西,拿论文要求来看,文章里面可能会有不足。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的文字越来越像八股文,油画系的学生写维米尔、伦勃朗,但是你有什么自己的新发现、新感觉?都没有写,灵光乍现的东西把它丢掉了。”

大师不是从天而降,生活也没有那么多的运气和意外,一切都是好的安排。就像狄更斯口中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尽力而为之,不负自己,时间总会在某一瞬间给你一个充满偶然的惊喜。中国美术学院高世名院长在今年9月的新生入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人》的讲话,他说,我常问同事们一个问题:这么多的年青人进入美院,是学专业还是学艺术?粗看起来,这二者并不矛盾,谁都知道专业训练是学习艺术的必由之路,但我想说的要点是——不能以狭窄的专业经验,掩盖甚至阻碍真实、广大的艺术经验。艺术应该让个人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丰富辽阔,而非越来越专门、越来越狭小……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像东坡这样,与自然、四季、雨雪、山谷那么亲近,就一定不会心思闭塞,一定不会有封闭的人生观。”
